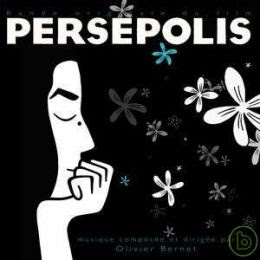上週四傍晚六點多,很快結束工作很快搭上計程車直奔西門町日新戲院。為了親眼再看一次大螢幕的《一一》,還有讓身體記得自己還有力氣趕上金馬影展最後一場電影。
楊德昌在九九年完成這部電影,我回想著自己透過哪些機會知道這部電影、看到這部電影、與人談了這部電影,直到這晚坐在貴賓席真正目睹這部電影,時序過了八年,這也可能是我踏入電影這一行的時間銘記。
家庭的故事總是最平反瑣碎,要用一種既世故、避免犬儒、既精準又兼顧感性溫厚的口吻,告訴觀眾一個關於華人家庭的故事,不過於矯情又不落入俗套,以楊德昌擅長的現代主義簡約風格,加上對現代社會精準批判力道,是絕對不會令人失望的。但當我這次再看<一一>,卻頭一次感覺楊德昌電影裡獨特的抒情靈魂,以及將家庭主題的電影敘事帶往一種史詩般的寬廣與厚度。
家庭的故事總是最平反瑣碎,要用一種既世故、避免犬儒、既精準又兼顧感性溫厚的口吻,告訴觀眾一個關於華人家庭的故事,不過於矯情又不落入俗套,以楊德昌擅長的現代主義簡約風格,加上對現代社會精準批判力道,是絕對不會令人失望的。但當我這次再看<一一>,卻頭一次感覺楊德昌電影裡獨特的抒情靈魂,以及將家庭主題的電影敘事帶往一種史詩般的寬廣與厚度。
A one and A two,是這部電影的英文片名,家庭裡每個成員都有相類似的處境與遭遇,只不過身分不同、性別不同、生命階段不同,每人生活裡卻持續上演著相類似的人生驚喜與困境。小兒子洋洋情竇初開,偷窺著初戀情人游泳、不會游泳卻也一頭栽進游泳池的天真,在爸爸N.J.面對初戀情人時的靦腆表現上,有著同樣的趣味呼應;母親在跟自己病塌上的母親重複說著一樣的話時,驚覺生活裡竟然一無所得的幻象破滅,與對愛情保有浪漫憧憬的女兒婷婷,在面對自己被欺騙時的驚嚇,兩人最初對人生持有的單純戀眷並無不同。
然而,震懾人心的不是這些成員每個人生命中,以"成長"作為子題的呼應,而是捕捉一個個現代個體,楊德昌冷靜犀利鏡頭中展現反思力量;例如,我們看到飾演媽媽的金燕玲,無助地面對自己的先生,不由自主顫抖哭泣覺得自己白活,一個中景,硬生生地對著她將近兩分鐘,完全不處理飾演N.J.吳念真的反應鏡頭,所營造的疏離感讓我們不得不覺察觀看者(我們自己)的處境,而且也只有透過銀幕,更能真實映照自我困境的虛無與假貌。
最終,每個中途離開的角色,還是回到家裡,在婆婆的告別式上團聚;家庭成員之間出軌、受挫、流動情感相繼被取代、滿足、補位,就像這場有和煦陽光灑下的午後,舉辦的告別式中,大家一起等待,讓每個人靜靜排隊與婆婆做最後一次的告別,象徵一種迎接每個人再次回到家中的儀式,殘酷的告別,卻是必要存在,也是楊德昌留給家這個概念(也是他留給這個世界),以一次輕盈卻溫暖筆觸寫下的完美終曲。
我想,因為這部電影,總會讓我想起不小心踏入這行的最初情感,在某個重要生命的場景中,我還是會再拿起這部電影的DVD,溫習自己生命裡的重複循環與新生經歷。